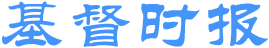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从历史反思偏见》,为什么要从历史反思偏见呢?这是出于我对历史的一个基本看法。我们了解和学习历史,不仅是回到当时、当地和当事人那里,有所谓同情的了解,理解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作出那样的决定。我们也要从历史当中,发现一些人性普遍相通的东西,理清文化和历史的深层次的内在理路,能够给我们今天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提供帮助和参考。
那为什么又要从明清之际讲起呢?因为这一段历史,应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回看中国古代历史,真正意义上能达到所谓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深度接触交融的时期,首先是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其次是晚清民国。其他时间,比如汉代之前,殷商周秦主要是诸子百家,中原文明内部互相碰撞和融合。到了汉代,才有印度的佛教进来,和儒家、道教开始碰撞。到了唐宋元,儒释道的主流逐渐形成,濂洛关闽的新儒学成型,相对于这个主流,尽管也有摩尼教、也里可温,也有其他北方和西域民族的文化,但都是支流,大面积的影响很少。直到明末,天主教来了,这个文明高度不是其他支流可比,吸引了一群很有代表性的儒家精英,开启了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碰撞和交融,虽然清代中断了,到晚清又开始碰撞,直到今天还是在继续。所以怎么理解这个大问题,不仅对中国人、对儒家人士重要,对包括新教在内的广义基督宗教很重要,对未来中华文化怎么走,怎么演变,怎么发展的观察来说都很重要。
明清之际,中国文化里最精英的人士,跟西方文化最精英的人士之间直接面对面的对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英国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他就讲这是两大文明之间联系的最高范式。也有汉学家讲这是中国跟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最高层的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是中西关系史上一个非常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段历史,其实不仅是中国文化或儒家文化跟西方天主教文化之间的接触。在晚明,除了阳明学兴起,除了东林学派兴起,其实晚明的佛教也有复兴,还有像李贽、汤显祖这样倡导人性解放的文艺界的复兴,所以当时是一个交织错落的思想界的盛况。那么,从这段中西碰撞、百家争鸣的历史中,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呢?今天,我就从一张地图开始讲起。
大家看到这张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收藏在南京博物院,这是4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相对完整的世界地图。也就是说,四百多年前,中国的读书人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模样了,不再是什么中央之国、唯我独尊了,而是中国处在五大洲当中的一小部分,其他部分比如说西欧也有璀璨的文明。这张地图的背后,其实反映了四五百年前的中国读书人已经睁眼看世界,不只是200多年前魏源、林则徐才开始睁眼看世界。那么,这张地图的背景是什么呢?是李之藻帮利玛窦印出来的。500多年前,一群传教士利玛窦他们他们从欧洲到达中国,生活在中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翻译,和中国文人士大夫交往,从明末到清初,长达150多年,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有些在中国,有些保存在梵蒂冈、意大利、西班牙。
利玛窦在1583年进入中国大陆,之前在澳门停留,他的前一任领袖罗明坚进不来,再往前的连澳门也进不来,沙勿略去了日本。除了利玛窦,耶稣会里还有很多精英,比如罗明坚是第一本汉语外语词典《葡华词典》的作者,艾儒略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地理专著,邓玉函是伽利略的朋友,所以当手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后,他就把望远镜第一个带到了中国。非常神奇。汤若望也是典型代表,他当时把西洋火炮带来了,也编译了第一部火炮方面的书。还有谁呢?比方说,卫匡国,他被誉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因为他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相对完整的地理学著作,他当时还见证了满清入关,进入中原和江南,他是第一个目睹的,然后把它写成书,放到阿姆斯特丹去出版,这个变成世界上第一本记录明清改朝换代的一本书。还有金尼阁,利玛窦的助手,他是把儒家的五经翻译成拉丁文,传回西方去出版,然后他也是最早把《伊索寓言》翻译成中文的人。所以四五百千年,晚明的中国读书人是可以读到《伊索寓言》的,当然他们读的不是我们现代白话文的版本,而是文言文。
我们看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为什么他们在500多年前,坐半年一年的船,跨越三大洋来中国?这种事不太可能发生在安土重迁、志在当官的中国读书人身上。这群传教士也有自己的背景。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危机,很多教会慢慢变成新教了,脱离了天主教的管辖范围。所以,当时天主教的精英们也在呼吁内部革新和海外宣教。耶稣会就这样应运而生。
1534年,耶稣会的几个代表性人物,罗耀拉、沙勿略他们就在巴黎大学创办了耶稣会,这个会出身的基因里就自带学术属性,他们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推进天主教的内部改革,但是怎么改呢?他们非常重视教育、学术、神学研究、苦修、海外宣教,也非常重视社工慈善。五六百年来,耶稣会在世界上办了很多教育机构,今天还有100多所大学、学院、高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有耶稣会的背景。今天你去美国,可以看到波士顿学院、乔治城大学、圣路易斯大学,还有日本的上智大学,韩国的西江大学,都是耶稣会办的。还有台湾的辅仁大学,耶稣会也参与了。
耶稣会背后的思想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把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和基督信仰融合在一起,注重从古典语言对圣经的诠释,去修正中世纪对圣经的诠释,然后回到早期基督教,进行温和的改良,同时注重学术教育的训练,提升人的智性和信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修会,也只有这样的修会才能训练出利玛窦这群人出来。
利玛窦从小就进入耶稣会的学校,在意大利那边,开始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的训练、信仰的苦修,所以他的人文修养、知识结构非常深厚,同时抗压能力也很强,去过印度实习了几年,那时1578年,当时中国海禁还进不来,1582年到了澳门,过了一年进入广东,然后一路北上,到南昌、南京,最后到北京十年,1610年在北京去世,今天墓地还在北京党校里面。从1583年到1610年,将近30年时间,他都生活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直接跟当时中国最前沿的文人精英对话,要达到这个程度是不容易的。今天,也不见哪个西方的传教士可以直接跟中国最前沿的知识分子深度对话。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出来的,而且他不仅是学术思想,知识上的训练,长达十多年,他还要去传教。他还要出去,这个到印度,到中国这些很远的地方,要融入到当地的文化里面,所以这个不仅是读书人那么简单,他还要走出书斋,走出修道院,要去到一个异文化、异语言的地区,还要跟那里的知识精英发生深度对话,这个难度非常之高,也正是耶稣会能够培养出像利玛窦这样一群特殊人物出来。其他修会,比如道明会就比较难了。
另外一面,中国这边有哪些人出来跟这群传教士交流呢?也都是非常精英的知识人,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徐光启,还有李贽、黄宗羲、方以智和他爸爸,东林学派的邹元标,白鹿洞书院等。基本上,这群人里面受到阳明学的影响,占到很大比例。后面我们会讲到,为什么阳明学派和各个分支、书院的人,后来有些直接变成天主教徒,或者至少亲近天主教,给传教士带路和引荐。这跟阳明学在万历年间解禁和复兴有极大关系。
王阳明是1529年去世的,也就是在利玛窦进来之前的60多年,王阳明就去世了,那么在嘉靖年间,包括张居正这个当政的时候,禁止王阳明思想的传播长达50年之久,一直到万历年间才解禁。这时候,阳明学在社会上已经是显学,思想传人都有谁呢?徐光启就是,他算是泰州学派的,他是焦竑的学生,焦竑又是罗汝芳的弟子,也跟过王艮的儿子,他们都是泰州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了。1600年,徐光启在焦竑家里认识了利玛窦,3年以后就皈依受洗,隔年中了好几次都没中的进士,从此开始了正式的仕途。
泰州学派里还有谁呢?李贽也是,还有汤显祖,都是这一脉。还有东林书院这群人,也是阳明后学,尽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回归朱子学。东林学派的影响力主要在南京和北京这两个首都,很多官员都在东林学派的人际网络里。这群人对传教士非常友好,也扮演着晚明思想解放的开路者、引领者的角色,也正是这群人能够积极接待从西方过来的传教士,眼界和思想比较开阔,不像程朱学派那么固守华夷之辨。
当然细讲的话,也有例外情况,比如蕺山书院的刘宗周和他的学生黄宗羲,同样也是阳明后学,但他们对传教士和天主教就比较排斥和反对,当然他们也排斥泰州学派那群人,认为是王学左派,落入狂禅,走偏了。黄宗羲最后在《明儒学案》里都没把李贽写进去。当然这是另话了。我的意思是大家要了解中国文化里这些深度的脉络纹理,不然你了解到都是粗线条,没法真切地体会历史深处的模样。
第二部分
利玛窦是如何跟这群中国士大夫打交道的呢?清代礼仪之争时,康熙曾提到“利玛窦规矩”,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第一,奉行上层路线,结交文人士大夫,还有给皇帝送礼物,用“交友”的方式,而不是“传教”的方式进入中国的精英群体。事实上确实有效,至少利玛窦在东林学派、阳明后学的群体里很受尊敬。第二,编译一系列西方自然科学和道德哲学,通过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农学等吸引和结交士大夫,最后慢慢引向神学和教义。第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合儒-补儒-超儒”的路线,当然这条路线在张星曜那里有了完整总结。合的是先秦原始儒家,补是用天主教补充宋明理学的不足,排的是佛学和道教,最后完成超越儒释道,归向天学。第四,就是对中国的传统习俗保持宽容态度,皈依天主教的儒家士大夫可以祭祖、祭孔,在祖先牌位前点香行礼。
其实,与此同时,根据利玛窦向耶稣会总部写的报告里,他还提到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比如他提到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天主教和这群传教士好奇呢?其实也并非全部是因为上面四个方面,也因为中国人对这群传教士的记忆力高超和炼金术很好奇,才过来交流。
所以,这群人无论是简单的好奇,是对自然科学的部分好奇,或是对神学的部分好奇,还是抱着敌意和反对的心态,总之这就慢慢形成了一个新的关系网络。我们可以从这张“意义的网络”里看到各方对外来思想的理解,看看他们分别是从什么角度,从什么尺度去理解的,这里面就不仅仅是历史了,还关乎意义的重新诠释。
我们来看看他们各方是如何理解的,我们一步步推导,到最后会触达更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理解、偏见是如何产生,如何运转的。只有厘清这里面的机制和逻辑,我们才能更清晰地面对所谓的“跨文化对话”的问题,或者两大文明之间碰撞和融合的问题。
先来看这群传教士是怎么理解的。以利玛窦为例,他在《天主实义》里讲得很清楚:
“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与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过一人,修居于武当山,俱亦人类耳,人恶得为天帝皇耶?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
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了,相当于他对天主教、儒家和道教之间三家的“判教”,认为“天主”和原始儒家《尚书》《诗经》里多次提到的“上帝”是一回事,跟道教说的“玉皇”不是一回事,他认为后者只是由人修炼而来,并不是自有永有的造物者和至高神。
另外,利玛窦在《天主实义》里也辨析了身体和灵魂的关系,灵魂的存在,世间万物的次序,反驳佛教和道教的世界观、人观,这里不展开,都是用儒家语言在描述天主教神学(经院哲学)。这本书非常重要,它系统展现了天主教的神学,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之外开出了“第四教”,也就是天主教,或者以“儒家一神论”为主要特征的“天学”。
信奉“儒家一神论”的“儒家基督徒”,就是跟利玛窦走得最近的这一群人,成了第一代皈依天主教的儒家士大夫,包括“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也包括王徵、冯应京等人,他们都是“积极的诠释者”,当然他们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重新诠释。复旦李天纲老师曾说,儒家基督徒不是天主教神学的被动接受者、复述者,而是积极的诠释者。很大程度上来自欧洲的这群耶稣会传教士们要传播什么?怎样传播?这些事务不是在欧洲决定,而是在中国的江南地区,由神父和儒生们一起讨论决定。
那么,尽管这群“儒家基督徒”或者“天学”的追随者、建设者都是积极的诠释者,但他们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说跟他们各自的人生际遇、文化关怀、政治抱负等息息相关。
徐光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可以看他给利玛窦著作写的序言、跋言,也看下他在南京教案时护教的《辩学章疏》。他在给《二十五言》写的跋里提到:
“盖其学无所不窥,而其大者以归诚上帝,干干昭事为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诸凡情感诱慕,即无论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绝不萌诸其心,务期扫除净洁,以求所谓体受归全者。间尝反覆送难,以至杂语燕谭,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盖是其书传中所无有,而教法中所大诫也。”
他认为利玛窦的学说涵盖很广,无所不涉,但核心就是以侍奉上帝为中心,甚至到一个地步,每时每刻、每个呼吸都以此为中心,对每一个念头都加以检查,一旦萌发无此无关的念头,都及时扫除干净,达到全人、全身心侍奉上帝、顾念上帝的地步。他还认为利玛窦的天学,本质上和讲究忠孝的儒家是一致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后来在《辩学章疏》里也提到可以“补益王化”,帮助中国人返归尧舜禹三代之治。
我们从徐光启对利玛窦的诠释中,可以看出徐光启侧重从修身养性、身心道德,以及三代之治的文明秩序的角度,支持天学的传播。这跟李之藻、杨廷筠的角度有略微差异。同样都是“圣教三柱石”,李之藻是怎么理解的?
他说:“尝读其书,往往不类近儒,而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篇,默相勘印,顾粹然不诡於正。” “唐虞之世,自羲和治历,暨司空、后稷、工虞、典乐五官者,非度数不为功。《周官》六艺,数舆居一焉。而五艺者,不以度数从事,亦不得工也。襄、旷之于音,般、墨之于械,岂有他谬哉?精于用法而已。故尝谓三代而上,为此业者盛,有元元本本,师传曹习之学,而举丧于祖龙之焰。汉以来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虚发无效。或依拟形似,如持荧烛象,得首失尾。至于今而此道尽废,有不得不废者矣。” “第儒者不究其所以然,而异学顾恣诞於必不然”“不徒论其度数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 “彼(利玛窦)其梯航琛贽,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不闻有所谓羲、文、周、孔之教。故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濂、洛、关、闽之解。而特於“知天”、“事天”大旨,乃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而是编者出,则同文雅化,又已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赞教厉俗,不为偶然,亦岂徒然?”
李之藻认为利玛窦带来的天主教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恰恰是中国人遗失的“古学”,也就是上古曾经出现过的学问,只是后来丢失了。他还认为利玛窦在来中国前,都没听说过周孔之教,也不懂濂洛关闽的理学,竟然“如券斯合”,真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这是李之藻的理解,他特别从自然科学、古学的角度进行诠释。事实上,李之藻刻印《坤舆万国全图》、翻译天文学《浑盖通宪图说》,算学《同文算指》,以及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等,大都涉及自然科学,这是他的终生兴趣,也是他对利玛窦带来的新学说的最深刻的体会。大家可以看到,徐光启和李之藻就存在很大不同。
关学的代表性人物王徵,他本来是朱子学的传人,但是到他45岁的时候,读到了庞迪我的《七克》,这本书也很重要,主要讲天主教有关“罪”的神学探讨,后来在中国传播比较广,不仅儒家士大夫读,很多和尚道士也读。
1615年,王徵已经45岁,照理说应该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很稳定,但是他读到这本书后,大受感动,他原话是说:“见其种种会心,且语语刺骨,私喜跃曰:是所由不愧不作之准绳乎哉!”已经到了“会心”“刺骨”的地步了,可见对他精神影响有多大。
王徵后来写了很多书,包括《畏天爱人极论》,就说“予于是日,似喜得一巴鼻(古时口语,意思是标准或根据)焉者。随与庞子时时过从,相与极究天人之旨。窃谓果得一主以周旋,自可束我心神,不致走放,可训至不愧不怍无难也。”他认为在传教士庞迪我那里,看到了信仰的状态,就是有一位主和自己互相周旋对话,可以约束六神无主、心神游离的状态。
后来,他在《仁会约引》里总结说:“夫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超义实,大旨总是一仁。仁之用爱有二,一爱一天主万物之上,一爱人如己。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然必真真实实,能尽人之心之功,方是真能爱天主。”用今天的话来说,王徵理解的天主教就是——“畏天爱人”,或者“爱天主,爱人如己”。他的角度更多是从灵性的角度,从个体与天主在精神层面的相遇来理解天主教,而不是从自然科学,或者从返归三代的政治秩序的角度去理解。
总之,不管是徐光启,李之藻还是王徵,他们的角度多么不一样,但最后都皈依了,成了“儒家基督徒”,在他们那儿,儒家和天主教并不矛盾,反而是十分如券斯合,不仅没矛盾,而且相得益彰,天主教给儒家补充了儒家一开始就有但后来丢失了的东西。所以,这是他们的理解路径。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积极的诠释者”,也有“消极的诠释者”,其中以佛教人士最严厉。当时的净土宗八祖、杭州的莲池大师(云栖袾宏)专门写了《天说》来批判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他认为:“按经以证,彼所称天主者,忉利天王也,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此一四天下,从一数之而至于千,名小千世界,则有千天主矣。又从一小千数之而复至于千,名中千世界,则有百万天主矣。又从一中千数之而复至于千,名大千世界,则有万亿天主矣。统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称最尊无上之天主,梵天视之,略似周天子视千八百诸侯也。彼所知者,万亿天主中之一耳。余欲界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而色界诸天,又上而无色界诸天,皆所未知也。又言:“天主者,无形无色无声。”则所谓天者,理而已矣。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赏罚乎?”
这句话我们今天看来有些搞笑,事实上当时他就是这样认为的。莲池大师认为佛教的“诸天说”比利玛窦的“天主”合理得多。佛教认为有很多重天,每一层天都有这层天的主人,而天主教的“天主”只不过是其中一层天的主人,叫作“忉利天王”,远远不是终极的存在。而这个终极的存在,在莲池大师看来是客观存在、无形无声的“理”,没有人格特征,不会像天主教说的那样还会赏善罚恶。这一点,其实背后不仅是佛教,也有宋明理学的影响。
后来,黄宗羲在晚年著作中不但批评了天主教的天主,也批评了佛教的诸天说,他是站在阳明后学、刘宗周这一脉的“气性论”的角度来看的。
黄宗羲是晚明三大儒之一,也是浙东经史学派的开创者,开启了清代学术的脉络,他读过很多传教士编译的著作,也研究过西方数学以及哥白尼的天文学,可以说是视野非常开阔的儒家。
不过,黄宗羲对天主教的宇宙本体论是持批判态度,他在记录刘宗周学说的《孟子师说》里,认为天地间“全是一团生气,其生气所聚,自然福善祸淫,一息如是,终古如是,不然,则生灭息矣。此万有不齐中,一点真主宰,谓之‘至善’,故曰‘继之者善也’。”就是从“气性论”的角度建立他的宇宙本体论,从这点来反对天主教里带有强烈人格化特征、甚至参与人类具体历史的“天主”或“上帝”。
另外,黄宗羲甚至对“上帝”这个被天主教拿过去使用的词语,也进行了辨析,他认为:“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公之摄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则抗乎祖,欲遂无配,则已有仁父之心。”“于是乎名天以上帝以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假令天若有知,其宰制生育,未必圆颅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天,引天以近之,亲之也。”
对于这点,我曾经有篇短文做过分析,简单来说就是黄宗羲认为“上帝”只是一种描述亲近的称号,并不直接能指称最高存在。“天”尊而不亲,“上帝”亲近人情。进而,最高者是“天”,而不是“上帝,人格化是对最高存在的一种描述,本质上其实是“降格”。
黄宗羲虽然一定程度上赞成耶稣会士对佛教的批判,以及对“天”的推崇,但他决不赞同耶稣会士对“天”的人格化与历史化(立像记事),后者也已涉及犹太-基督宗教的核心层,亦即上帝的位格以及救赎历史的问题。
晚明士人许大受写了一本《圣朝佐辟》,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他认为“辟者何?辟近年私入夷人利玛窦之邪说也……念此邪徒,祸危实甚,而窃儒灭儒,人所叵测,日炽一日,靡有底归。今且夜授妇女,不避帏簿之嫌;挥镪聚民,将有要领之惧。”什么意思?许大受认为天主教是偷窃儒家的东西,为了灭掉儒家。
到了清代,纪晓岚却认为天主教是偷窃了佛教的东西。很有意思,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去评价天主教。纪晓岚是清代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但他对天主教的理解却是认为偷窃佛教。
这是他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提要》里,对利玛窦《二十五言》的提要:“《二十五言》,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利玛窦撰。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言,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
清代的氛围已经跟晚明很不同了,汉族知识精英竟然认为天主教剽窃佛教,让人感到很震惊。当然,《二十五言》其实还不是天主教的核心义理,主要来自古罗马斯多葛学派爱比克泰德的《手册》,加入非常少量的天主教神学,用儒家语言翻译过来。
但是,不论如何理解这本不是天主教神学的小册子,或者联系一下《四库全书》里收录的利玛窦的其他著作如《天主实义》等,也不应该认为剽窃佛教。这还不如许大受所认为等剽窃儒家来得更有说服力。可见,各方的诠释五花八门,带有很浓重等时代背景。
在晚明还有一个人,对利玛窦及其带来的学说相对友好,但是并为皈依,而是保持有距离的欣赏和适度的批评。他就是李贽。我们知道李贽受到泰州学派的影响,但很有个性和自由思想,他后来甚至住到了芝佛院里,对儒家的礼教秩序非常反对,主张回到人的“童心”,挣脱礼教或名教的束缚。那么,李贽怎么来看利玛窦呢?他大概跟利玛窦见过五六次面啊,其中三次在焦竑的家里见到利玛窦,对利玛窦的学说也有一定的了解。
李贽在《与友人书》里提到了利玛窦,他说:“承公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国十万余里,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四万余里矣。及抵广州南海,然后知我大明国土先有尧舜,后有周孔。住南海肇庆几二十载,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礼,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仆实,数十人群聚喧杂、雠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斗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则过诌,非露聪明则太闷闷瞆瞆者,皆让之矣。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
简单来说,李贽认为利玛窦不像当时的一些儒生那样谄媚或闷闷,而是一个非常标致正宗、贯通四书五经的儒家,但是他对于利玛窦想用天学来取代周孔之学,又认为他太愚昧。所以这是李贽的理解角度。我们知道,李贽后来是连礼教都反对的人,非常倡导独立个性的人,就像他在《焚书·赞刘谐》《续焚书·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里面戏谑孔子一样,他认为孔子也是平常人,人人皆可成圣,又何必专门把孔子的学问当成正脉,甚至抬高到至圣先师的地步呢?可以看出,李贽不但批评儒家,也批评利玛窦的学说,而他的批评跟许大受,或者后来的纪晓岚的批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在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群体,虽然并没有像圣教三柱石一样皈依,但对传教士的态度却是比较友好的,他们就是东林学派。这个后来很多学者说成“东林党”,也有学者研究当时并没有一个作为实体的党派,而是一个松散的、互相应和政见的学派,相对符合史实。东林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邹元标,他对利玛窦非常友好,他认为:“得接郭仰老,已出望外,又得门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岛而见异人也。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门下取《易经》读之,乾即曰统天,彼邦人未始不知天。不知门下以为然否。”
邹元标认为利玛窦传讲的东西其实跟中国这些圣人们非常接近,只不过孔子这些人把利玛窦的学说发挥得更加详细,所以他认为利玛窦跟儒家是不冲突的,因为都是在讲同一个东西。
十七世纪巴尔托利(Bartoli)在 《耶稣会历史》也说: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在东林书院主讲过。神父们对东林党表现出巨大热情,大力称赞东林书院的道德标准。同时“书院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的友好感情。”
也正是这一层关系,使得耶稣会在南京、北京能获得较长的和平时间,因为这两个地方就是东林学派里做官或者讲学最多的两个地方。所以,很多事的背后都有当时特殊的时空脉络。
前面我们说了纪晓岚,其实在清代康熙皇帝也值得一说,为什么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传播了150年,从晚明到清代,那到康熙皇帝这个时候,礼仪之争不可开交到极致,最后禁教,驱赶传教士了呢?要知道,一开始康熙对天主教很友好,他甚至还为耶稣钉十架写过诗歌——《十架颂》,现在还收录在很多版本的《赞美诗》里,但是后来态度从友好转变为不友好,甚至禁教。这里面不得不说“礼仪之争”,这件事本身很复杂,可以另外专题来说。
简单来说,最开始耶稣会进入大明后,采取比较温和的“利玛窦路线”,容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供奉祖先牌位,但是后来耶稣会第二代领袖龙华民不同意,想用“陡斯”(Deus)取代使用“上帝”一词称呼圣经里的那位至高神,当然也禁止信徒祭祖祭孔,认为是与信仰冲突的异教行为。不过,这件事在1628年嘉定会议已经内部解决,耶稣会决定祭祖沿用利玛窦规矩,译名采用龙华民方案。
然而,这件事涉及的根源问题并未解决,特别是后来进入大明的其他修会,不像耶稣会那样注重人文主义和文化宽容,比如多明我会就很反对耶稣会宽容尊孔祭祖,上诉教廷。1645年教廷反对耶稣会的方案,1654年卫匡国前往梵蒂冈去解释,到了1656教廷又改为支持,后来换了教宗,1704年又禁止尊孔祭祖,禁用“上帝”“天”,教宗克雷芒十一世甚至发出八条禁约,统一使用“陡斯”(Deus),不能祭孔,不能进祠堂或孔庙行礼,吊丧不许行礼,还不许在家保留排位,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牌位上有灵魂。所以,这就几乎推翻了耶稣会的路线。到了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又颁布“自登基之日”的通谕,重申必须绝对遵守1704年的禁令,所有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否则将受逐出教会的处罚。
这件事来来回回,变了好几次,最终这件事也惹恼了康熙。当时,康熙为澄清中国礼仪之争,派遣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艾若瑟出使,但在收到教宗的答复后,他说:“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
很明显,康熙的态度从积极互动到冷漠拒绝,最终禁教,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公开传播到此结束,长达150年的耶稣会路线结束,部分天主教徒还存留在河北、河南、江南、闽东的农村地区,改为地下模式,多数传教士退到澳门,或者回西方,也就是又回到利玛窦他们最开始进来的地方。
到这里为止,我们说的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和中华文化长达150年的交融、碰撞的历史,暂告一段落,下次回来要到清末了。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提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儒家,也有佛教,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部分支持和部分反对者,也有误读的人。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没有一致方向性的存在,那种单向度的叙事肯定是有问题的,必然经过某种角度的选择和编写。真实的历史里同时存在很多种声音,各自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做出理解。
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有没有相对一致的某种内在理路?它不一定是类似科学原理那样整齐划一的逻辑,而是人们进行理解活动的相通的理路。接下去,我想从诠释学的角度,从“前理解”“偏见”“期待视野”“接受意识”来谈谈这些人不同诠释的背后,所存在的理路究竟如何影响他们的理解活动。我想,厘清了理解活动的深层理路,我们才能对纷繁现象进行适度的提炼和升华,才能对我们当下的理解活动产生一定的参照作用,尽管它并不是精准整齐的。
第三部分
面对明清之际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众说纷纭的跨文化对话以及不可避免的误读,如何厘清这里面的发生原理或者内在理路?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同样,太阳底下无新事,并不是说历史现象都是相似的,那不太可能,因为时空环境都在变化,但是其中的内在理路极有可能是相似的。
我想今天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深处外来宗教、文化、思潮和原生文化的碰撞和激荡中,身处各种各样的主义、学说、理念的碰撞里,我们对此会发生非常多的理解,里面有反对的,有接纳的,有皈依的,有冷漠的,有保持距离的,有反感的,今天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态度,我们怎么去看这些态度?不被表象迷惑,而是去看深层的理路,这里面就有人文学的基础,非常内在的视角。
诠释学是西方哲学思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支,当然早期是对圣经的诠释、圣经学里面慢慢发展出来的,到了启蒙运动以后,它越来越变成一个独立的学问和复杂精细的学科。我这里主要借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小试牛刀,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通过诠释学来重新理解这些文化现象。
诠释学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认为人类在理解活动中,无法根据某种超脱的“客观”立场,超越时空去作出“客观”的理解。所有理解必然必然产生偏见。虽然理解的目的是为着克服主体及其时空偏见,去认识作品的客观意义,但是人又不能脱离各自的历史性,人的历史性恰恰构成理解活动的基础。如果没有人的历史性,没有文化的传承与积淀,理解活动便无从发生。
因此,在本体论层面,这种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偏见是合法的存在、合法的偏见。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种“偏见”,在纷繁现象中呈现它,并使其成为理解活动中的积极因素。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就认为,这种偏见是一切理解和诠释的必然,都必然经过且依赖于传达者与接受者的“前理解”。
海德格尔强调先行结构对人的理解活动的影响,而伽达默尔说得更加彻底:“说到底,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的理解”。对文本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固定线性的活动,而是不断的揭示和敞开。
当然,在前理解中,也包含了合法的前理解与盲目的前理解,前者因为文化在历史中的传承,在人的理解上存在著文化的沉淀,使人的理解活动不得不与这种文化积淀发生联系。而后者,则因现实权威、封闭视域等造成,使人盲目理解,造成不合事实的误读。
合法的前理解与盲目的前理解,有时混杂在一起,并不会直接显露出清晰的层次,这就需要让各种前理解在理解活动中显现出来,甚至坦承会出现偏见的事实和风险,从而用真诚的对话、辨析的方式,来不断消解盲目的前理解。既然偏见是不可避免的,那就从偏见出发开始对话。
如果说偏见与前理解带有本体论意义层面的不可去除性质,是无法避免的先在结构。那么,期待视野与接受意识,既与作为先在结构的前理解有关,也与当下的存在与互动影响息息相关、不断生成。
什么是“期待视野”?这是姚斯接受美学里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一个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之前,不是一片空白的,而是带有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的,他是带着自己的一种预先估计和期待,去面对这个作品的。这种期待可能是好奇、热爱、沉醉、为我所用、无所谓等,都是一种种心理期待,也正是这种期待,让理解活动得以发生和运作。
所以说,对某个东西的意义的阐发,是传达者与接受者两者互相融合的产物。对于接受者而言,并不是传达者怎么传达,他就百分百等比例接受,这是不可能的,一定会变异。他在理解活动之前的前理解、期待视野,还有他在理解活动中的接受意识,都会交织影响他的理解和诠释。
那么在对话过程中,既需要传达者(作者)的“创作意识”,也需要接收者(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意识”。传达者的意图能否实现,作品的客观价值如何,需要依靠读者的“接受意识”。期待视野与接受意识相辅相成,在人的理解活动中,互相影响,形成动态的关系。
举个例子,你在来听这个讲座之前,一定是有自己的前理解,从你出生成长,通过教育、家庭、工作、社会经验,甚至看手机新闻、刷抖音微博,你在头脑里肯定已经形成一种理解的结构,带有你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但是当你来听这个讲座时,如果突然听到一个跟之前你活了三十年都没听到过的新的信息,让你很震撼,你的态度一定会产生共鸣、反对或者同情。这很自然,每个人都不会例外。有人说,我保持沉默。但是,沉默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没有言说的内在理解。
所以说,关键不在于你具体什么态度,而是你的、他的、我的、他们的各种各种的态度,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其中有没有相通的原理?如果你站在这个高度去看问题,你就不会陷入自己或别人的态度或观点里,而是会跳出来,看清其中的逻辑或者原理了。
理解这些原理以后,我们结合明清之际耶稣会和儒家士大夫之间150年的接触和对话,看看他们各自的“前理解”、“偏见”、“期待视野”、“接受意识”都是什么样的?怎么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诠释甚至误读?以及这些误读都是如何慢慢发生的?
比如,徐光启为什么从儒家士大夫变成了第一代儒家基督徒、天学的信奉者?因为他带有自己的前理解,他是一个追求事功的典型文人,所以对天学的理解也有强烈的“返归三代”的前理解和期待视野,对利玛窦的理解也是把他看成“西儒”“利子”这样的正宗儒家形象。再看看他的学脉,他是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传人,视野比较宽阔,认为西海东海、心同理同,这也为他接受天主教,奠定了前理解的基础。事实上,当时最欢迎利玛窦的中国士人,很大比例是阳明后学的群体,不管是泰州学派的焦竑、徐光启,还是东林学派的邹元标。
同样是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但是他们皈依的理由和触发点是不一样的,也反映出每个人的接受意识不一样。比如李之藻本身就有对科学的强烈兴趣,在利玛窦的学问和知识仓库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自然科学,皈依以后他也着重引介这部分的学问,而不是其他。冯应京和杨廷筠感兴趣的主要是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部分,徐光启比较看重农学、数学等可以作用于国计民生的学问。尽管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兴趣和期待,但最后都皈依了。
黄宗羲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和数学感兴趣,也很积极地学习,但他并没有像李之藻那样皈依,他对天主教本身是排斥的,因为他毕竟是刘宗周蕺山学派的传人、浙东经史学派的开创者,还是儒家的本位和主体性,有明显的华夷之辨。我们可以看到最中心的这几位大儒,对天主教都没有皈依。徐光启也算是当时的中心人物,但在经史之学上,还没有达到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这样的中心地位。在儒家的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中心还是边缘,或者介于两者之间,都会影响到他是否脱离原先的结构,进入新的结构中。当然,即使他进入新的结构,也不是焕然一新、改头换面重来,肯定还带有原来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双重结构,比如形成了融合儒家和天主教的“天学”或者“儒家一神论”。
在这个两大文明的碰撞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光谱,看到圣教三柱石、南明皇室的“皈依”,也就是“完全投身”,但这种“皈依”又带有各自的前理解。我们也可以看到李贽、泰州学人、东林学人的“欣赏但不皈依”,可以看到黄宗羲等人的“部分接纳、部分反对”,可以看到刘宗周、莲池大师和佛教居士的“完全反对”,也可以看到康熙的“从欣赏转为反对”。他们的各种态度,其实都凝结在这张诠释的意义网络上,只是所占的经纬度不一样而已。
我想,这个讲座时间有限,但到这里基本已经给大家展示了一种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进入历史的深层肌理里面,去分析他们的前理解、期待视野,去分析他们所占的意义网络的节点和经纬度,这样理解历史和文化现象,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也能对我们当下所处的意义网络的节点有所理解。我就是这样看待文化现象的,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