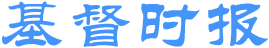第二章 永远也不要害怕任何人、任何事
什么都不要怕
“此世永远也不要害怕任何人。”我仍然记得这句话,仿佛是我昨天刚刚才听到的。说此话的人是格罗夫·帕特森(Grove Patterson),地点是旧版《底特律日志》(the Detroit Journal)的编辑办公室,时间为1920年的10月份。
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记者,我的老板正在给我布置任务,后来他成为了我终生的朋友。他用一根光秃秃的、带着墨渍的手指指着我。他的手指头上似乎总是会有墨水。“听我说,诺曼,以后也永远不要忘记这句话。不要吓得浑身打哆嗦、也不要因为某些恐惧而战战兢兢地生活。世界上究竟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猜他看我看得很透彻,因为恐惧和极度的自卑感多年来一直都在给我添麻烦,让我痛苦不已,直到我学会了如何克服。而格罗夫·佩特森的这一番话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要直面别人,直面事物。直视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都滚开。对你自己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不会害怕任何人,任何事。’每天都要对自己说这句话,而且要说很多次,直到这句话深深烙印在你的脑海里。”
那天我的老板对我的影响真的非常大。他将自己的话和他自己具有男子汉气魄的信仰烙在了我的意识里。生平第一次,我看到了一丝希望,一丝可以打败我的恐惧的希望。他似乎能够看出我在想什么,他又说了一句更为有力量的话,而这个位于杰斐逊大街的破破烂烂的编辑部也因为这句话而变得明亮起来。
直到今天,我仍然能够回忆起当格罗夫慢慢地道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那种力量:“你当刚强,你当勇敢;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不论你在哪里,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 1:9)
他友好地拍了拍我,说道:“从恐惧中出来吧,老伙计,竭尽全力地去摆脱它!”像这样的经历,你总是会不时地回想起来,以从中获取继续生活下去所需要的新的活力。
从那时开始,我就日夜不停地努力,以达到控制恐惧的目的。一开始我的动力还主要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因为当时我已经厌倦了总是害怕、害羞和紧张。我一定要放松和释放,不然的话,我会崩溃的。我坚决不希望一辈子都这样遭受着恐惧的折磨。我再也不能带着恐惧生活下去了,因此我才下定决心要克服恐惧。
可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格罗夫·帕特森说宗教信仰能够帮助我。好吧,我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年轻人。我父亲是一个传教士,直到上大学之前我一直都在教堂里混。在之后的四年里(我都有点羞于启齿了),除了我父母来看我的时候,我基本从来不去教堂。这也许是因为我与教堂的接触太多,也或许是因为大学教堂里的传教士们并不能打动我。不过我也必须承认,我其实并没有给过他们多少机会。
放假回家的时候,我每个星期天都会去听我父亲的布道。他是与众不同的。他所讲的都是一些有气魄、实际、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且他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坐在讲坛下面的人们的热爱。他在早年间曾经是一个医生,而且从他在密尔沃基的行医和地位来看,他曾经也一定是一个好医生,因为他当时的办公室就在密尔沃基。
在生了一场大病之后,他经历了一次独特的精神转换,此后他就再也无法离开牧师这个行业了。他总是能够将医学和宗教融合在身体、心智和灵魂的整体当中。他信奉《圣经》,也信奉精神体验,同时他也是一位有着很强的社会意识的敏锐、没有偏见的思想家。
在思想、表达和方法上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他显然也不会循规蹈矩。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在听他布道以及与他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他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且非常不同:他所信奉的,是一种能够真正与一种有力的、康复性的、可以改变心智的力量共同作用的基督教。我清楚地看到,当心智得到了痊愈之后,人的身体和灵魂也会受到影响。我也明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真理,即人类的很多疾病,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都源自于灵魂上的病态。
从我父亲所强调的实用宗教当中,我开始明白,我自己的矛盾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这让我开始了对心灵安宁的探索,对战胜我自己的探索,以及对我所确信的基督教所赋予我们力量的探索。我并没有立刻就找到了这些。其实这是一种为时很长的探索,而且过程往往令人感到非常沮丧,但是我却找到了很多。因此,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也感觉到了牧师这个行业对我的召唤。
后来我进入了波士顿神学大学学院(Boston University of Theology),但是我当时正在苦苦寻求能够解答我自己的问题的答案,在这里并没有找到。神学院的教师们一开始就试图动摇我“简单”的信仰,取而代之以一种知性的方法来研究耶稣的教义,这让这些教义成为了一种社会宣言。他们将此称之为“社会福音”方法,意为将基督的教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
他们认为,相对于似乎已经成为老古董的“个人福音”或者拯救人类的灵魂和心智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更为高级。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个人福音和社会福音——放在“整个或完整的福音”里去考虑和衡量。但是我当时觉得神学院的那些老师、教堂领导和超级聪明的学生都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也成为了所谓的社会福音的忠实拥护者。
但是,在我向人们教导这种高级的社会福音几年之后,我开始怀疑它并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了。我原本所拥有的个人精神领悟力和精神力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迂腐。而且普通人来到我的教堂的时候,似乎只有当我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跟他们谈论上帝通往更好生活的方式时,他们才能够被感化和吸引。
我开始质疑社会伦理型的基督教,质疑它是否能够真正带来个性的改变。我意识到,在个人支持以上帝为中心的社会福音之前,他们在个人的生活当中更加需要上帝。在这种备受强调的社会福音之下,我看到,人们在个人精神生活上开始恶化。
就这样,因为我当时正陷入了一种内心的困境之中,所以我开始一页一页地翻阅《新约》,希望能够找到这种社会福音的明确的纲要。我当时非常幼稚,我以为《新约》是耶稣基督真正教义的、唯一的权威文件和基本文件。但是我的这些学者朋友们告诉我,不要读《新约》,而要把那些来源不明确的问题查阅弄清楚,他们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棒的真知灼见”。
我被这种高级的智慧深深的震撼了(这是我之前恐惧症的后遗症——我一直都对学者和能言善道的人怀有一种敬畏之情),所以我就在这些所谓的“最棒的真知灼见”当中寻找着我的答案。但是很快我就开始提问题了:这些真知灼见是谁的?他们到底知道些什么?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即使是这些最棒的真知灼见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 13:8)。
我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耶稣的教义的主要目的,是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培养出虔诚的人。如果消除他们身上的异教信仰,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就会开始关心自己的人类同僚。他们会像兄弟一样对待彼此,会尊敬所有的人类,而不管他们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或者什么地位。
他们会努力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好,尤其是“那些小个子的人”(《马可福音》9:42),即那些弱小或者不幸的人。我明白,开明的社会原则就是来自于这样的基本教义。但是我永远也无法赞同下面这种狂妄的假设:要想成为一个基督教徒,我必须领导人们进行一次罢工或者加入某个社会主义党派,或者让议会通过某项立法,或者称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为反动派。
我注意到,在自由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两个阵营当中有些极端主义者,他们是那么的自负,卑鄙得那么彻底。所以我决定走中间路线,与那些不是非常精明也不傻的人在一起,他们并没有一切的答案,他们也清楚自己没有答案。但是他们却在谦卑地寻求上帝。
我从神学院毕业后,加入了布鲁克林的一家教堂,这个教堂只有40个成员,教堂的主体结构很小,而且已经有些残破不堪。我满怀热情地加入了这个日益壮大的社区,努力想把这个教堂壮大起来。我爬楼梯,使劲跺人行道,运用我所掌握的所有方法去感化人们。
我把他们一个个地引进了教堂,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教堂的成员发展到了将近一千人,我们也拥有了一幢不错的崭新的教堂。我不断地努力,希望能够将社会福音和个人福音所传达的教义融合到一起。我总是在强调,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在基督的周围,并且屈从于上帝,那么生活将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我们有一群快乐而美好的教众,他们的快乐完全是来自于彻底的献身精神。我父亲富有活力的信仰就这样通过我而传达给了这些教众们。这一点其实非常奇怪,因为我绝对是上帝所利用的最靠不住的工具之一。
后来我被调到了位于锡拉丘兹的一个很大很漂亮的教堂。这个教堂的结构非常宏伟,基本上完全是用巨大而美丽的窗户建成的,这些窗户都嵌在石头里。我到现在仿佛仍然能够看到,在阳光明媚的周日早上,当阳光透过艺术玻璃照进来的时候,投下了一束束强烈光线,从四周有圆柱支撑的圆顶上倾泻而下。
这是一个大学的讲道台,现在仍然受到一些学者们的敬仰,尤其是那些假装深刻的人,我在这里进行了一些真正的“知性”讲道。然后有一天,一位名为迪安·布雷(Dean Bray)的教授请我吃饭,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说:“不要试图用学问镇住我们。虽然我们都是教授,但我们首先都是人,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事实。
你是我们的精神老师,你要将生命之食粮掰成非常细小的小块,这样我们才能够消化它们。你只要展现你的真我,因为我们需要你来告诉我们,上帝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上帝为你个人做过些什么。”这就是这个伟大的教授给我提的一个明智的建议,那就是要简单。
可是问题是,我当时已经刚刚失去了我之前曾经拥有的精神活力。而且事情还不仅如此。之前的那些恐惧和烦人的自我怀疑仍然在折磨着我,我在心智和情绪上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矛盾。我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我的心智深受巨创,以我当时宗教信仰的深度、活力,或者领悟力并不足以治愈这种创伤。
虽然对于基督教来说,这种了不起的伦理和社会模式是可行的,它也的确已经开始主宰美国自由新教,但是对我而言,它就是不能令我满意,也没有任何的效果。如果它连我一个人都无法改变,那么它又如何去改变任何事情,当然更不用说社会了。迫不得已,我仍然需要找到真正起作用的模式,不然的话,事情会变得很糟糕。更何况我也知道应该去哪里找。
此后,我开始对那些曾经在个性上经历过重大和深刻改变的人展开严肃的科学研究,例如酒鬼、小偷、放荡之人等,还有一些曾经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煎熬,但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之前的困难的人。几乎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都能发现,带来这种令人惊讶的改变的,是对耶稣基督的一种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信从。
虽然上述的所有问题都不是我自己的,但是我也有其他的一些困难,其复杂性和导致折磨的程度和上面所提到的问题基本相当。我曾经饱受恐惧、害羞、自我质疑、无能感和巨大的自卑情结之苦。
向耶稣基督信从的行为,能不能像我的研究对象那样肃清我的所有这些弱点?我坚信是可以的,虽然除了从我亲爱的“父亲”巴特斯那里曾经听到过类似的事情之外,我从未在波士顿大学里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尽管巴特斯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教授,他会去学生那里看望学生,与他们谈话,与他们一起祈祷,并且慈祥地问他们:“你们现在是在做‘好孩子’吗?”
但是我却发现,在我从神学院毕业之后的几年里,我无法充分利用这种救赎方法。在我克服了一个知性方面的障碍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知性化的基督教领袖们似乎非常鄙视这种被“拯救”或者“改变”的事情,而我和他们之间的交往也让我羞于与这种救赎沾边。事实上,这种救赎基本上被认为是“迂腐陈旧的”。至少改变生活在“最棒的”圈子里是不被重视的。
至于罪恶,显然它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而已,它只是局限于资本家和共和党人,相对而言,显然神圣的劳动领袖们、左翼人士和超级世故的政客们是与罪恶绝缘的。从最新的传教士的嘴里,你几乎永远也听不到任何关于罪恶的话,除非是从理论的角度上对其进行谈论。
不过你倒是可以从为数不多的几个仅存的“反动派”的嘴里听到一些关于罪恶的话, 他们仍然对社会主义心存质疑,但是这些反动派们也很快就会被迫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传教士领袖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了。
一些奋兴大会(Revival meetings)也是备受鄙视的,例如那些由比利·森戴(Billy Sunday)主持的奋兴大会,还有最近由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那些知识分子们非常讨厌他)所主持的奋兴大会。这种奋兴的概念在自由主义基督教里也陷入了无用的境地。有多少次,我看着一些普通的大学毕业生竭尽全力地想让自己受到虽然博学但是没有精神没有生命的基督教的启发,例如比尔·琼斯(Bill Jones)、玛丽·史密斯(Mary Smith)和哈里·威尔逊(Harry Wilson),他们还想努力让自己对这种基督教产生兴趣。简而言之,其心灵和灵魂都已经不属于基督教的范畴了,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虽然他们仍然保留着外在的形式,甚至还会去教堂,并且捐钱给教堂,但是成千上万的人都会直接朝着地狱的方向走去。
在我的心智里,我已经云游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去了很多的地方,试图找到一种信仰的体系和一种实践这种信仰的方式,以让我获得对自己的个人胜利。如果我想要拥有去帮助别人取得胜利的能力,我首先要为自己找到胜利,不然的话,就会像是一个盲人领着另外一个盲人一同栽进臭水沟一样。
我开始阅读某种精神材料,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材料正在越来越多地涌入教徒们的家里,用其中所包含的教义去感染这些人。材料的来源有统一运动、心智科学、很多形而上学的老师们、基督科学会、牛津团契以及道德重整运动。格楞·克拉克(Glen Clark),斯塔尔·戴利(Starr Daily)和宋铭嘉(Sam Shoemaker)都是人们渴望拜读其作品的作家。这些作家们告诉人们,耶稣基督创建了一种思想和生命方式,它非常科学,也完全可行,能够给我们带来改变和胜利。我所读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让我想起了我父亲的布道,尽管在他自己的早年时期,并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作家的作品。但他也通过自己独立的对实际和具体教义的探索,得出了类似的概念,这些实际和具体的教义针对现代的人类,能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真正发挥作用。
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归正教会的一个忠诚牧师,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保守的基督教徒,而且现在仍然是。我真诚地相信,《圣经》就是上帝所说过的话,我的真诚程度和最彻底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当然我没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所坚持的华丽的词藻和机械论的方法。我完全接受救赎的方法。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圣子,是我们的主和我们的救世主。我相信圣灵,相信耶稣是圣贞女之子,而且,我也相信所有的使徒信条。
我完全赞同基督教堂的历史性教条,但是我也相信,这种古老的信仰是可以通过新鲜的思想和语言形式教授给人们的,也可以科学地运用到人们的生活当中,给人们带来创造性的力量。我还相信,这种古老的信仰也是可以解决人类本性和社会当中最困难的问题的。
每一次的打击,都能够让你变得更强
在我的布道和我出版的书里面,我一直都在传扬这种信仰,当然我也遭遇到了一些牧师相当大的反对。有几个人甚至专门组织布道对我进行抨击,把我的教义称为“皮尔主义”——自由主义者们谴责我是因为某个原因,而原教旨主义者谴责我则是因为另外的原因。不过这种经历,让我也对一句古老的谚语有了全新的体会:“每一次的打击,都能够让你变得更坚强”。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一次,我的教堂成员们聚在一起,开始轮流讲述自己为什么来到我们的教堂。有一个女的说:“是魔鬼把我带到了大理石学院教堂。”说这话的时候,她忍不住笑了起来——这让震惊中的听众们松了一口气。
她解释道:“我本来是某某牧师教堂的成员,由于他总是在布道中批评皮尔牧师,说皮尔牧师是‘魔鬼派来的’。他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个皮尔牧师,谈了很多次,所以后来我开始好奇,然后就去了皮尔牧师的教堂。
我发现人们正在排着队等待参加礼拜仪式。我听了那天的布道,我认为那次的布道是非常不错的圣经福音,所以我又有好几个礼拜日来此做礼拜。然后我回到了自己原来的教堂,而某某牧师仍然在布道批判皮尔牧师。所以在布道之后我走向他,问他:‘难道世界上有两个皮尔牧师吗?’他回答说:‘不,只有一个,诺曼·文森特·皮尔。’我说:‘哦,那就奇怪了。我一直在听他的布道,而他和你的描述一点儿也不一样。’他脸红了,”她继续向我们说道,“从此我就决定加入皮尔牧师的教堂。”
显然这些人不喜欢任何人用任何其他的术语或者思想形式来谈论基督信仰,除非是他们传统上所使用的那些术语或者思想形式。虽然我很确定他们在自己的想法上是非常诚恳的,但是显然对他们而言,任何人在方法和方式上与他们有任何的不同,都是应该遭到谴责的:似乎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是同一个模式。这些人现在可能感到非常烦恼,因为或许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种精神教义的传扬方式正在感染着非常多的人。
我从未对别人的不同意见表示过任何的反对,而且迄今为止,像太平洋宗教学院的院长罗伯特·菲奇神父(Rev.Robert F.Fitch)所使用的不太文雅(我们暂且这么描述吧)、不太友好、颇具讽刺意味的言辞,我也从未使用过。作为一个这样尊贵的学者,他却不太优雅地称我为一个街头小册子的分发者,还说:“皮尔的东西纯粹是巫术,和真正的基督教大相径庭,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这件事情上,我不得不承认,一位老采矿工程师曾经说过的一句非常友好、非常朴素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把《丹佛邮报》(Denver Post)所发表的一些评论送给了我。这位采矿工程师一定是一个有着令人感到非常愉快的性格的人,同时也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他评论道:“鲍勃·菲奇(Bob Fitch)博士应该向全能的上帝提一些问题。我一辈子都在与地质学教授们一起工作,我发现有了一个博士学位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话说得虽然有些粗俗,这毫无疑问,但是说的却是非常有道理。不管怎么说,这句话都让我备受误解的心灵得到了安慰。)
文人相轻
我一直都对我们的教堂领袖、神学院的领导和教授们怀着真诚的敬意,所以对于他们对我的激烈抨击,我感到很伤心。奇怪的是,这些攻击并不是针对我的观点的,而是针对我这个人本身的。
我一直都很奇怪,为什么有些牧师会变得那么的苦大仇深。虽然我很抱歉这样说,但是根据我的经验,一些最粗鲁、最不礼貌的话,其实并不是来自于普通教众、无知的人或者没有教养的人之口,而是来自于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传递福音的牧师之口。
人们会揣测,有些人会不会无意间把自己的仇恨和敌对掩藏起来,然后用博学的牧师语言将其发泄出来,虽然这种语言一般来讲不会像菲奇的话那么粗俗,但是也颇为伤人。这种因某个牧师同僚引发的奇怪的敌意,似乎格外地恶毒。
我这里指的仅仅是少数的几个人和某一种类型的人。总的来讲,牧师们都是可爱、真诚的绅士们,我也真心地尊敬他们。
不过我还是决定要忍受他们的攻击,为我的这些恶意的诽谤者们祈祷,尽全力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对我有着这种敌对的态度,但我仍然会因这些绅士们在其他方面的高效领导能力而尊敬他们,我个人从来没有对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有过任何的恶意。我当然要努力地把我自己的教义付诸实践,其中的一条就是千万不要让我的心智容得下对任何人的仇恨。
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对牧师这个职业的影响和权威感到敬畏,对于他们的攻击,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有一阵子我甚至已经下定决心要辞去牧师的职务,转而在有组织的教堂之外继续帮助人们。我甚至连辞职信都写好了。一想到这些,我现在都感到有点难以置信,我当时怎么会让这些人影响了我。
不过他们现在再也无法影响到我了,这是绝对的。这其中有几件事情阻止了我,让我没有离开教堂。其中之一,就是我所在教堂——美国归正教会——的人们对我的理解,我相信如果我说这个教堂是美国最和谐、真正自由以及真正的基督教机构之一,大家也会理解的。
另外就是领导和成员们的友谊,还有聚集在大理石学院教堂里数量巨大的来访者们,他们都是前来聆听我们的布道的,我们在布道中宣扬的,是上帝改变生活的简单的力量。无数人的生活正在被改变着,上帝保佑着我们这个教堂,我明白我必须要在美国最古老的教堂的讲道坛上,向世人们传达这个教义。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我认为我是对的。我不断地寻求上帝的指引,而当你认为自己做得对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勇气和支持。在我的祷告里,上帝似乎总是在告诉我,要继续用他的福音去帮助他的人们,用他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运用他们能够控制和使用的实际的方式,不要理睬别人对你的攻击。
我没有辞职到教堂之外工作的最后一个原因,是缘于我的父亲。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但是他的头脑和精神和以前一样敏捷。他说:“诺曼,我一直在研究你的书和布道,很明显,你已经逐渐地发展了一种思想和教导的新型宗教体系。很不错,非常不错,因为其中心和周围以及精华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牢固的圣经导向是毫无疑问的。没错,你在结合了心智科学、形而上学、基督科学会、医学和心理学实践、浸信会福音主义、卫理公会派和牢固的荷兰改革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基督教,其所重视的东西与以往不同。”
他说我发展了全新的东西,这一点我并不赞同。我何德何能,怎么能去发展一种新型的基督教?我并不是神学家,而只是一个传教士和牧师。“我所传扬的只不过是旧的福音而已,爸爸,”我说道,“只不过我使用的是现在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罢了。”
“这倒是真的,”他说道,“但是之前从未有人以这种方式这么做过,也从未做到过这种程度。你的工作是新和旧的结合体,而且你从来没有对耶稣基督和《圣经》不忠过。你传扬的是一种完整的福音,包括罪恶、信念、救赎、赎罪天恩和拯救,但是你对其进行了简化,让它变成一种实际而令人愉悦的生活方式。这完全是以耶稣为中心,而且是以人为本的。”
“可是,爸爸,”我说道,“那些显要的神职者和不那么显要却一成不变地追随领导者的神职者们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愤怒。我真的很想辞职,日后在教堂之外成立我自己的布道机构。”
他凝视着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我会心碎的。你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真正的传教士,你忠于教堂。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个老传教士的话,而且,”他继续说道,“皮尔家族的人从来都不会放弃。”那一番话最终让我改变了主意。我在教堂呆了下来。只要你的教义完全忠于耶稣基督,那么上帝的伟大教堂里是完全可以容得下不同种类的人和各种各样的方式的存在的。
《意志的力量》(一):www.christiantimes.cn/article-detail.php
《意志的力量》(二):www.christiantimes.cn/article-detail.php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