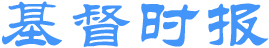当一个男人结婚成家,媳妇就成为这个家庭的外来人口,在新组成的核心家庭和大家庭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张力,这种张力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也表现着不同的形式。笔者有幸通过母亲的口述和童年的经历,将这一段时间的婆媳关系史整理出来。当然这仅限于我们那个村庄的案例,至于是不是普遍现象,留给读者去评判。
我奶奶的邻居嫁过来的时候还是旧社会,那时候媳妇没有什么地位,当然媳妇的地位取决于娘家人的势力,娘家有财有势的,媳妇在婆家也被高看一眼,因为娘家不仅物质上可以接济婆家,在政治势力上也可以将婆家人击垮,但是对于那些双方势力均等的人家,媳妇就没有什么优势。奶奶的邻居,我们暂称李老太吧,娘家是个农民,没什么土地,家境和婆家一样贫穷,所以在婆媳中处于服从地位。母亲讲过一件事情,这是李老太亲口所说众多事情中的一件。结婚后不久,李老太回娘家,当然那是农闲时期,对于纯粹种粮食的生产模式来说,一年忙碌的时候只有两个时候,就是种和收,这两个时期加起来也不过四个月,其他时间都是农闲。面对回娘家的媳妇,婆婆给的政治任务就是纺纱,在起身的当天给媳妇称好棉花,交代几天回来,回来的时候这些棉花要纺出纱来。等到媳妇从娘家回来的时候,婆婆把纺好的纱过秤,发现少了一两,婆婆很生气,认为媳妇娘家人克扣了棉花,大闹一顿,结果媳妇娘家人不得已只能把纱再补回来,这件事才算了结。在那个时候,婆婆一般有很大的权力,媳妇是不能反抗的,哪怕和婆婆顶嘴也不允许,除此之外只有一条解脱的途径就是自杀,但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十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些都反映当时真实的情况,这两句话也成为媳妇痛苦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力量,所以那个时代虽然媳妇受到很大压制,当他们做了婆婆的时候也要这么做,在那个环境中,婆婆已经形成一个固有的身份。配合婆婆权势的是村庄舆论,一旦这个媳妇被打上不孝顺的标签,她就会成为村里茶余饭后消遣的主题,即使与邻居因为小事吵架,也被骂“没老没少”,将来有了儿子也不好找媳妇,对于那个婚姻半径只有10公里的时代来说,这的确是个巨大的潜在危机。所以那个时代李老太选择的是忍耐。只是到她娶儿媳妇的时候,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我的伯母是远近闻名的精明人,与人吵架没有输过的。因为她家的势力强大,在我奶奶那边没受什么委屈。伯母娘家是大马子,大马子就是响马,当地的土匪,结伙成队去抢劫的帮派,在赛珍珠的《大地》里主人公王龙的叔叔就是大马子,所以王龙始终害怕他,无偿供他吃穿。堂哥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结婚的时候是70年前后,堂嫂娘家家境一般,加上堂嫂性格懦弱,所以堂哥和伯母从来没有分家,可能是因为只有一个儿子的缘故,所以堂哥一辈子就和伯母家生活在一起。伯母在我记事起虽然强悍,但只要不涉及家庭主权的问题伯母就不会难为大嫂,只要经济大权在握,对待堂嫂还是不错的,不像李老太的婆婆。虽然如此,堂嫂性格的懦弱在经过长期的抑郁之后,终于在四十岁上下脑溢血,最后半身瘫痪。这个时候物质生活已经慢慢好转,不再像以前那么贫乏,人和人之间那种紧张的争夺关系也有所缓和。村里通了广播,加上每个月一次的露天电影,婆媳关系不再是村民议论的核心话题。
我的邻居叫老黑,姓邱,因为曾经和我父亲一起用平板车贩卖石头时,我父亲救过他的命,所以我们关系颇好,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是老大,结婚的时候我五岁,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也是田地承包到户的第五年,全村已经没有饥饿的迹象,饥饿已经进入大家的回忆中。老黑的儿媳妇是拖拉机拉过来的,拖拉机后面拖个大车厢,用席子搭个帐篷,新娘子坐在里面,外面是伴娘围着。这比李老太被老公牵个毛驴就嫁过来风光多了。新媳妇过门不仅带来嫁妆,还带来土地,她的责任田也随着户口迁过来,这又是与李老太的不同之处。婚后不久,过了蜜月期,他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分家,因为老黑还有一个女儿要嫁,媳妇觉得过日子再辛苦不能给小姑子作嫁妆,并且现在自己也有了土地,脱离大家庭,营造自己的核心小家庭才是必须的事情。他们结婚是农闲的腊月,到了开春就要吵着分家,在李老太和我伯母那个时代,独生儿子是不能分家的,分家即为不孝顺,四世同堂还是普遍的理想状态。到了老黑媳妇,哪怕独生子也要分家已经形成一种趋势,这其中媳妇起主导作用。面对媳妇提出分家的要求,婆婆们显得极不适应,“不孝顺”这个时候成为婆婆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大家聚到一起就是诉说媳妇的不好。老黑媳妇春节一过,就闹着分家,大吵大闹,叫来了妇女主任,村长,生产队长等官方人士,最后不得已婆婆同意分家,把责任田、粮食人均分配,债务也一样分配,另外再给新家庭启动资金,分好家之后,婆媳并没有消停过,婆婆总是看媳妇不顺眼,横挑眉毛竖挑刺,但是媳妇并没有屈服。虽然分家但是还在一个院子里过日子,再怎么不顺眼也要过下去。八十年代中期村里年轻人开始做生意,当然也就是贩卖大米。老黑儿子和媳妇也在农闲时期做起生意,老黑女儿也去做了生意,未出嫁的女儿抛头露面,和男人们一起起早摸黑用自行车载大米卖,被村里老人们诟病,只要她从家出来,凡看到的没有不指指点点的。婆婆开始是和人讲媳妇的不是,后来干脆不论遇到谁就开始哇哇哭泣,觉得自己命不好摊上这样的媳妇。当婆婆由诉说到哭泣的时候,村子里做生意的未婚女孩开始增加,几乎一半的女孩都去做生意了,她们成为反面教材,后来八十年代后期因为堂哥女儿与生意伙伴谈恋爱,堂哥喝农药自杀未遂。过年的时候村里男丁都要给老年人拜年,不论是否同一姓氏,老黑媳妇面对每一个给自己拜年的人都要哭诉一番,拿出碗来说过年只给自己盛一碗饺子,吃不饱,等等。其实他们住一个院子,媳妇家的厨房并没有锁门,甚至连门都没装,婆婆吃完自己去装一碗完全没人反对,田里种的蔬菜也没装铁丝网,婆婆自己出去挖一篮子蔬菜也没有问题,只是媳妇不会把饭烧好端到床前罢了,婆婆年纪轻轻,这些动手就可以做的,所以婆婆的反应完全是面对媳妇崛起的不适应。这个时候村里的舆论开始分裂,年轻人,那些刚成家不久的媳妇,那些没有做婆婆的妇女完全没有把老黑媳妇的遭遇当作多大的事情,他们最多也就说一句,婆媳矛盾双方都有不好。倒是那些做了婆婆的老年人比较热心,倾听,议论,哀叹,完全引起共鸣。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村里最经常发生的吵架就是分家和婆媳矛盾。我的一个堂嫂也是那个时候喝农药自杀的,前面说到的堂嫂也是同一年脑溢血去世的。这个十年是婆媳冲突最大的时期,好不容易熬成婆的媳妇发现自己到头来还要受媳妇的气,这十年真是白熬了。媳妇因为经济地位的独立,也就敢于争取自己的家庭主权。这时的婆媳冲突完全是家庭支配权的冲突。
到了打工潮兴起的2000年,婆媳关系就发生质变了。我的堂弟结婚之前就出去打工,后来介绍隔壁村的女孩,结婚的时候是2010年前后了,结婚之后夫妻双方出去打工,第二年有了孩子,孩子就留给婆婆照顾,自己依然出去,后来生了二胎,加上堂哥脑血栓,媳妇就留在家里。他们谈不上分家,媳妇嫁来的时候除了作为嫁妆的家具之外,再无它物。大概2000年开始女儿出嫁已经不带责任田了,因为可以出去打工,田地已经没人关注。他们结婚后也不关心分家,因为自己的经济自己完全做主,与田地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婆媳矛盾也就无法产生。婆婆已经不能再要求媳妇把打工的钱上交了,整个村子舆论已经不关注不孝顺这个话题。因为可关注的事情太多。生了二胎,媳妇回家之后,妹妹已经出嫁,公公需要人照顾,但是婆婆尚且年轻,身体也不错,照顾公公没有问题。所以媳妇回家后,先把田地分开,在别的地方给公婆建造了房子,让他们分出去住,需要看病去看病,没有粮食给粮食,就是不要住在一个院子里。用村里老年人的话说,把老爹老娘赶到南地去了。但是村子里已经没人再去关注他们,也没人议论他们是不是不孝顺,对于婆婆来说这只能接受,不能提异议。因为在物质上不缺乏。虽然在精神上不会像以前一样享受凡事请示汇报的婆婆权柄。
到了今天,媳妇已经在核心家庭中占有主权地位,也很少有因为分家吵架的,或者结婚之后不分家的。如果有不分家的情况,也是媳妇掌握经济大权,但是不分家的不多。往往是婆婆年老多病,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媳妇把她接到家里照顾。所以当我另一个堂哥在父母提出分家,他哭哭啼啼不愿意分的时候,受到左邻右舍的嘲笑,认为他是假惺惺的孝顺。
社会在不断变迁,城市化加快了这个变迁的速度,虽然我们村婆媳之间愈来愈独立,按照传统文化是越来越不孝顺,但是这个过程依然无法阻止。在笔者看来这恰是进步,因为核心家庭取代主干家庭已经无法逆转。婆媳关系唯有在这个时候也才是健康的。
城市,颠覆了农村的社会结构。
当一个男人结婚成家,媳妇就成为这个家庭的外来人口,在新组成的核心家庭和大家庭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张力,这种张力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也表现着不同的形式。笔者有幸通过母亲的口述和童年的经历,将这一段时间的婆媳关系史整理出来。当然这仅限于我们那个村庄的案例,至于是不是普遍现象,留给读者去评判。
我奶奶的邻居嫁过来的时候还是旧社会,那时候媳妇没有什么地位,当然媳妇的地位取决于娘家人的势力,娘家有财有势的,媳妇在婆家也被高看一眼,因为娘家不仅物质上可以接济婆家,在政治势力上也可以将婆家人击垮,但是对于那些双方势力均等的人家,媳妇就没有什么优势。奶奶的邻居,我们暂称李老太吧,娘家是个农民,没什么土地,家境和婆家一样贫穷,所以在婆媳中处于服从地位。母亲讲过一件事情,这是李老太亲口所说众多事情中的一件。结婚后不久,李老太回娘家,当然那是农闲时期,对于纯粹种粮食的生产模式来说,一年忙碌的时候只有两个时候,就是种和收,这两个时期加起来也不过四个月,其他时间都是农闲。面对回娘家的媳妇,婆婆给的政治任务就是纺纱,在起身的当天给媳妇称好棉花,交代几天回来,回来的时候这些棉花要纺出纱来。等到媳妇从娘家回来的时候,婆婆把纺好的纱过秤,发现少了一两,婆婆很生气,认为媳妇娘家人克扣了棉花,大闹一顿,结果媳妇娘家人不得已只能把纱再补回来,这件事才算了结。在那个时候,婆婆一般有很大的权力,媳妇是不能反抗的,哪怕和婆婆顶嘴也不允许,除此之外只有一条解脱的途径就是自杀,但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十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些都反映当时真实的情况,这两句话也成为媳妇痛苦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力量,所以那个时代虽然媳妇受到很大压制,当他们做了婆婆的时候也要这么做,在那个环境中,婆婆已经形成一个固有的身份。配合婆婆权势的是村庄舆论,一旦这个媳妇被打上不孝顺的标签,她就会成为村里茶余饭后消遣的主题,即使与邻居因为小事吵架,也被骂“没老没少”,将来有了儿子也不好找媳妇,对于那个婚姻半径只有10公里的时代来说,这的确是个巨大的潜在危机。所以那个时代李老太选择的是忍耐。只是到她娶儿媳妇的时候,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我的伯母是远近闻名的精明人,与人吵架没有输过的。因为她家的势力强大,在我奶奶那边没受什么委屈。伯母娘家是大马子,大马子就是响马,当地的土匪,结伙成队去抢劫的帮派,在赛珍珠的《大地》里主人公王龙的叔叔就是大马子,所以王龙始终害怕他,无偿供他吃穿。堂哥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结婚的时候是70年前后,堂嫂娘家家境一般,加上堂嫂性格懦弱,所以堂哥和伯母从来没有分家,可能是因为只有一个儿子的缘故,所以堂哥一辈子就和伯母家生活在一起。伯母在我记事起虽然强悍,但只要不涉及家庭主权的问题伯母就不会难为大嫂,只要经济大权在握,对待堂嫂还是不错的,不像李老太的婆婆。虽然如此,堂嫂性格的懦弱在经过长期的抑郁之后,终于在四十岁上下脑溢血,最后半身瘫痪。这个时候物质生活已经慢慢好转,不再像以前那么贫乏,人和人之间那种紧张的争夺关系也有所缓和。村里通了广播,加上每个月一次的露天电影,婆媳关系不再是村民议论的核心话题。
我的邻居叫老黑,姓邱,因为曾经和我父亲一起用平板车贩卖石头时,我父亲救过他的命,所以我们关系颇好,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是老大,结婚的时候我五岁,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也是田地承包到户的第五年,全村已经没有饥饿的迹象,饥饿已经进入大家的回忆中。老黑的儿媳妇是拖拉机拉过来的,拖拉机后面拖个大车厢,用席子搭个帐篷,新娘子坐在里面,外面是伴娘围着。这比李老太被老公牵个毛驴就嫁过来风光多了。新媳妇过门不仅带来嫁妆,还带来土地,她的责任田也随着户口迁过来,这又是与李老太的不同之处。婚后不久,过了蜜月期,他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分家,因为老黑还有一个女儿要嫁,媳妇觉得过日子再辛苦不能给小姑子作嫁妆,并且现在自己也有了土地,脱离大家庭,营造自己的核心小家庭才是必须的事情。他们结婚是农闲的腊月,到了开春就要吵着分家,在李老太和我伯母那个时代,独生儿子是不能分家的,分家即为不孝顺,四世同堂还是普遍的理想状态。到了老黑媳妇,哪怕独生子也要分家已经形成一种趋势,这其中媳妇起主导作用。面对媳妇提出分家的要求,婆婆们显得极不适应,“不孝顺”这个时候成为婆婆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大家聚到一起就是诉说媳妇的不好。老黑媳妇春节一过,就闹着分家,大吵大闹,叫来了妇女主任,村长,生产队长等官方人士,最后不得已婆婆同意分家,把责任田、粮食人均分配,债务也一样分配,另外再给新家庭启动资金,分好家之后,婆媳并没有消停过,婆婆总是看媳妇不顺眼,横挑眉毛竖挑刺,但是媳妇并没有屈服。虽然分家但是还在一个院子里过日子,再怎么不顺眼也要过下去。八十年代中期村里年轻人开始做生意,当然也就是贩卖大米。老黑儿子和媳妇也在农闲时期做起生意,老黑女儿也去做了生意,未出嫁的女儿抛头露面,和男人们一起起早摸黑用自行车载大米卖,被村里老人们诟病,只要她从家出来,凡看到的没有不指指点点的。婆婆开始是和人讲媳妇的不是,后来干脆不论遇到谁就开始哇哇哭泣,觉得自己命不好摊上这样的媳妇。当婆婆由诉说到哭泣的时候,村子里做生意的未婚女孩开始增加,几乎一半的女孩都去做生意了,她们成为反面教材,后来八十年代后期因为堂哥女儿与生意伙伴谈恋爱,堂哥喝农药自杀未遂。过年的时候村里男丁都要给老年人拜年,不论是否同一姓氏,老黑媳妇面对每一个给自己拜年的人都要哭诉一番,拿出碗来说过年只给自己盛一碗饺子,吃不饱,等等。其实他们住一个院子,媳妇家的厨房并没有锁门,甚至连门都没装,婆婆吃完自己去装一碗完全没人反对,田里种的蔬菜也没装铁丝网,婆婆自己出去挖一篮子蔬菜也没有问题,只是媳妇不会把饭烧好端到床前罢了,婆婆年纪轻轻,这些动手就可以做的,所以婆婆的反应完全是面对媳妇崛起的不适应。这个时候村里的舆论开始分裂,年轻人,那些刚成家不久的媳妇,那些没有做婆婆的妇女完全没有把老黑媳妇的遭遇当作多大的事情,他们最多也就说一句,婆媳矛盾双方都有不好。倒是那些做了婆婆的老年人比较热心,倾听,议论,哀叹,完全引起共鸣。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村里最经常发生的吵架就是分家和婆媳矛盾。我的一个堂嫂也是那个时候喝农药自杀的,前面说到的堂嫂也是同一年脑溢血去世的。这个十年是婆媳冲突最大的时期,好不容易熬成婆的媳妇发现自己到头来还要受媳妇的气,这十年真是白熬了。媳妇因为经济地位的独立,也就敢于争取自己的家庭主权。这时的婆媳冲突完全是家庭支配权的冲突。
到了打工潮兴起的2000年,婆媳关系就发生质变了。我的堂弟结婚之前就出去打工,后来介绍隔壁村的女孩,结婚的时候是2010年前后了,结婚之后夫妻双方出去打工,第二年有了孩子,孩子就留给婆婆照顾,自己依然出去,后来生了二胎,加上堂哥脑血栓,媳妇就留在家里。他们谈不上分家,媳妇嫁来的时候除了作为嫁妆的家具之外,再无它物。大概2000年开始女儿出嫁已经不带责任田了,因为可以出去打工,田地已经没人关注。他们结婚后也不关心分家,因为自己的经济自己完全做主,与田地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婆媳矛盾也就无法产生。婆婆已经不能再要求媳妇把打工的钱上交了,整个村子舆论已经不关注不孝顺这个话题。因为可关注的事情太多。生了二胎,媳妇回家之后,妹妹已经出嫁,公公需要人照顾,但是婆婆尚且年轻,身体也不错,照顾公公没有问题。所以媳妇回家后,先把田地分开,在别的地方给公婆建造了房子,让他们分出去住,需要看病去看病,没有粮食给粮食,就是不要住在一个院子里。用村里老年人的话说,把老爹老娘赶到南地去了。但是村子里已经没人再去关注他们,也没人议论他们是不是不孝顺,对于婆婆来说这只能接受,不能提异议。因为在物质上不缺乏。虽然在精神上不会像以前一样享受凡事请示汇报的婆婆权柄。
到了今天,媳妇已经在核心家庭中占有主权地位,也很少有因为分家吵架的,或者结婚之后不分家的。如果有不分家的情况,也是媳妇掌握经济大权,但是不分家的不多。往往是婆婆年老多病,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媳妇把她接到家里照顾。所以当我另一个堂哥在父母提出分家,他哭哭啼啼不愿意分的时候,受到左邻右舍的嘲笑,认为他是假惺惺的孝顺。
社会在不断变迁,城市化加快了这个变迁的速度,虽然我们村婆媳之间愈来愈独立,按照传统文化是越来越不孝顺,但是这个过程依然无法阻止。在笔者看来这恰是进步,因为核心家庭取代主干家庭已经无法逆转。婆媳关系唯有在这个时候也才是健康的。
城市,颠覆了农村的社会结构。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