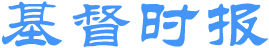纪录片若要拍的动人,不仅仅需要有故事,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人性能够激发共鸣。2007年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的《颍州的孩子》就是这样一部难得的佳片,尤其它不仅记录了现实,也改变了现实——让公众了解到因为母婴感染而不幸出生就带有艾滋病毒的那些儿童们,并且晓得面对艾滋病人,我们需要除去很多的偏见和歧视。
这个短片中的主人公是两个出生和成长在安徽阜阳颖州的孩子:13岁的女孩楠楠和4岁的男孩高俊。他们的眼神是那么的质朴,然而清澈之中却已经透出许多的麻木与冷漠。这两个出生就带有艾滋病毒的孩子,到底是如何生活的?而周围的环境又是带给他们怎样的压力,以及温暖?
纪录片《颍州的孩子》:被忽视的艾滋病孤儿群体
这是讲述艾滋病儿童的纪录短片首次挺进“奥斯卡”的大门。它真实而细致地讲述了艾滋病儿童的生存状态,其中以生活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地区的艾滋病儿童高俊和楠楠的真实生活为主,立体、详细且全方位地对他们二人进行叙事。
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拉开帷幕。一望无际的荒芜田地上,稀稀拉拉坐落着几座孤坟,在旁边一颗高耸却凋零的枯树陪伴下,更显凄凉冷寂。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13岁的楠楠就坐在离门很近的板凳上,门口站着她16岁的姐姐,两个人呆呆地望着门外,眼睛里透着与年纪不相符合的冷漠与麻木。她们的父母因卖血得了艾滋病双双去世,奶奶叔叔伯伯都远离了她们,两姐妹在破旧的房子里过一日算一日。
而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高俊,年仅4岁的他早已承受了太多不属于他这个年纪该承受的东西——艾滋病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父母,小小年纪的他跟精神有问题的奶奶住在一起。满目苍夷的房间里,他慢慢走到门口,村里其他的小孩子就在不远处嬉闹,他的玩伴却是满地乱走的鸡、鸭、猪,以及一条大黄狗。当镜头拉近时,能清楚看到在他脸上、手臂上、腿上起满了的皮疹。他就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低垂着头,稚嫩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的天真与单纯,有的只是对人生、对命运的漠然与敌视。

(因艾滋病感染去世之人的孤坟)
整个影片没有任何的加工与修饰,而是以写实的方式将病痛下脆弱而美好的生命展现在镜头前。影片的整个前半段基调都是灰暗的,冷寂中带着无以言喻的苍白、凄凉、孤独和死亡感;但从中间开始,颜色逐渐开始变得明亮起来,或许是新年到了,震耳欲鸣的鞭炮声带来了热闹的气氛之余,也驱散了长久以来掩盖在头顶的一丝乌云,楠楠的姐姐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楠楠因为姐姐结婚而脸上展露出久违的笑容;高俊也被一户人家收养——还离大门很远之时,那户人家的哥哥便冲出来抱着高俊进去,走到门口,早已在门口迎接的女主人也过来将高俊一把抱住,不住说:“我的孩子,长得真好……”
随着春天的到来,万物的颜色也逐渐变得缤纷多彩,和几个邻家小姐姐一起奔跑在田间小路上的高俊,脸上洋溢着的是从未有过的欢笑。被养父抱着走在种满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上时,高俊扬起手中的一株油菜花朝前面的哥哥挥舞,白净的小脸上充满了稚嫩的笑容,他说:“你过来拿花呀~给你哦~”尽管他的话语仍不够流畅,但他的笑声却回荡在乡间的田野间,久久不曾散去……
面对艾滋病人:去除“谈艾色变”,呼唤零歧视
本片没有直接的呼吁与呐喊,只是以写实的方式将贫穷、疾病、儿童、愚昧、冷漠、隔离、生命、盼望等一一展现。如何关注艾滋病人群及艾滋病儿童?除去给与物质上的帮助之外,精神上与灵魂上的帮助与救赎,才是影片想要诠释的最终意义。
而同时对于公众,透过短片,更多了解到我们需要抛弃那种“谈艾色变”的偏见,不该边缘化这些艾滋病人,而是更多了解和关爱他们。
当然,提到艾滋病,我们仍会感觉遥远。但网易新闻2016年一篇报道上指出,中国疾控中心统计,截止到2015年年底时,我国发现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计57.7万人,经测算估计全国人群总感染率约为0.06%,也就是说,每一万人中有6人“染艾”。并且,有多达32.1%的感染者未被发现。
在过去,很多人对于艾滋病的认识停留在“会传染”和“很可怕”的层面上,网上似乎也有各样的流传:“握手就会传染”、“一起吃饭会被传染”,甚至“被同一只蚊子叮过也会传染”……各样的谣传造成大众一度谈艾色变。事实上,对艾滋病的误解是一把会刺伤艾滋病患者的"利剑",倘若我们不扭转对艾滋病人的看法,这把利剑会严重地伤害到病人的身心。2014年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时曾强调说,“谈艾色变”的老思想必须要抛弃,要给艾滋病患者更多的关怀。
否则,没有人知道他们,也没有人关爱他们,艾滋病人会成为一群被他人放弃、被社会边缘化的“孤儿”。灵魂的救赎,需要人性的温暖。
《颍州的孩子》拍摄导演米子:希望有更多人通过影片帮助这些孩子
日前,基督时报同工邀请到《颍州的孩子》纪录片的拍摄导演米子老师,请她来谈一谈这部几年前纪录片拍摄时的前后经历与感想。
基督时报:您是2003年开始去拍这个电影的,当时为什么想到要拍一个儿童艾滋病的纪录片呢?
米子:2003年之前我一直在忙于工作,拍的多是电视剧。当时我已经觉得很累了,一些过来片子无论剧本喜不喜欢我都需要拍……那时我想,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会变成一个疲惫的机器人,而且有一次因为拍摄太辛苦导致自己完全失声,医生就建议我休息一年。那一年我去了一家4A广告公司,本想藉着这个机会休息调养一个阶段,没想到比拍电视剧的时候还累,后来我感觉这样下去不行,我真的需要重新调整下。
在那之前,其实我跟美方导演杨紫烨有过合作,我们一起拍了贫苦儿童的纪录片等。2003年时北京有个男孩子叫宗永飞(化名),他是第一个感染艾滋病的大学生——因为输血而感染的患者,当时他在筹备一群艾滋病孤儿画展,画展在北京的798工厂里面展出。那个时间段我恰好在北京,就去看了这个画展的筹备情况,并通过这个画展认识了他,赞助了他画展的部分经费。此后我也跟着他去了医院,还去了孩子们画画的地方,看了后内心极其触动,非常想要帮他完成这个画展——当然,最后画展也确实是完成了。
在完成画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收到清华大学景教授打来的电话,他说:“米子,阜阳有个患艾滋病的小孩子快死了,你赶紧跟你的团队过去拍下这个过程吧!”当时听完这话,我心情异常沉重,我想:天啊!我要去记录一个即将死去的孩子吗?这太残忍了……
我想了想,最终还是决定,如果他真的快要死了,我就不拍了,因为这太揪心了。但景教授说,这个孩子应该不会活了。他那样回答一瞬间又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想:我还是赶紧先去看看这个孩子,之后的事之后再说。当即,我就跟我的摄影师曲歌去了阜阳。
去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他是被阜阳艾滋病救助协会关爱着的。艾滋病救助协会的张颖女士一直关心着他。去了后,张颖女士带着我们去了那孩子——高俊的家。进门后所看到的场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是夏天,一个4岁的小孩子身穿着一条粗布的黑裤子,裤子长到将肚子都遮住了,他的上半身光着,头发因长期没有打理而全部揪在一起,脸上身上到处都是疾病起的疙瘩……苍蝇在他身体上飞来飞去、爬来爬去。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旁边有几只猪、几只鸭、几只鸡,还有一条狗在地上转来转去。在他身后的桌上是一小块几天没有动过的玉米,因为天气太热,苍蝇和蛆虫都从玉米里往外爬……

(纪录片中的小主人公之一 高俊)
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们才知道一直就是他的奶奶在照顾他。但是他奶奶是精神有问题的……一个70多岁精神有问题的奶奶,照顾一个才4岁的孩子……其实他是有叔叔伯伯的,叔叔伯伯家里也有健康的小孩,但由于他这个病,所以那些亲戚就把他隔离开,根本不认他。
这个孩子的父母亲是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而双双去世。我看到这个画面时就特别揪心,当时就哭了。后来我们就试着帮他剪头发,给他洗澡,让他能变得干净。在这整个互动的过程里,他的眼神都是敌视中带着一种漠然,仿佛在问:你们是谁?你们怎么会侵入到我的生活里来?对我们没有任何亲近感。
做完这些后,我们发现他一句话都没说,4岁多的孩子,正是爱表达的年纪,但他却一句话也不说,更没有笑容,很麻木的任由我们给他洗啊剪啊,他始终一言不发。我觉得这样不行,怎么也得让他开口。但想尽了办法,无论我们怎么做,他就是不说话。无奈之下,摄影师曲歌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买个儿童用的录音机送给他,里面有讲故事、小孩子的音乐等,我想,至少可以先让他慢慢地适应外界的声音。
这样,我们看完他之后就走了。但走之前我们和张颖说:“这个孩子我们会一直来关注的。”
其实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去探视的人心里也很乱。得了艾滋病的小孩不止他一个,另一个孩子艾滋病患者楠楠,也是这附近村庄的。当时她不过就12、3岁,正是上学的阶段,因为有这病她不能去学校,不能正常上学。
楠楠的一个婶婶也是这个病,所以村里人对她的关注没有高俊那样的不好,但她照样是跟其他孩子隔开来的。尤其是你看到她吃药时的痛苦——她吃药的时候会把药瓶子用力地摔,因为太难吃了,但她知道又不能不吃。
在回去的车上我们一直在想,怎么去帮助这一群孩子?那个时候还很“谈艾色变”,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跟一个艾滋病人握一下手,我都要花半天时间站在太阳底下“消毒”;跟一个艾滋病人吃完一顿饭,我回去感觉一个礼拜吃不下去饭;我们去村里的时候,把袖子口都拿橡皮筋扎起来,就怕苍蝇飞过来都带着病菌。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懂这些基础知识,后来慢慢发现,周围有一些人他们是健康的,但他们会跟艾滋病人很亲密地在一起,我才开始真正去了解艾滋病相关的知识,就发现之前那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也正是因为对艾滋病有了正确了解,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决定,要去完整地拍这群孩子。目的一是想要把他们的现状透过画面表达出来,让社会去关注;二是我们在整个拍的过程里,我们也会给孩子带去一些帮助。我们想跟着他们一起成长,看到他们点滴的变化。
就这样,我们花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在两地来来回回跑,那段时间就一直做这件事。
以前我也经常参与公益片的拍摄,但只是有时间就去做,没时间就算了。而这次开始我从内心觉得,我需要去做一点公益的事情。所以这两年里我基本上是纯公益地在做这件事。
每次去,我们都把带的钱全部拿出来给孩子买东西,觉得他需要什么就买什么,看到他有需求我们就去准备好。半年后的一天,拍摄的时候,在一个油菜花田里,孩子跟他的伯伯第一次出来玩,伯伯背着他在肩上,孩子就摘了一株油菜花咬了一口,吃了一下,露出了非常难得的灿烂笑容。当时看到这个画面,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孩子他会很健康地活着。因为在那之前,他没有笑容,也不说话。

(因父母卖血得了艾滋病 她们饱受世人的歧视)
基督时报:当时除了你们,还有别人帮助这些孩子吗?
米子:其实在这之前,这个孩子是有政府和艾滋病协会的人在资助他,每个月政府会给他400元的生活补助。但因为他奶奶自己也有病,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到他。后来通过艾滋病救助协会把这个孩子放到一个也有艾滋病患者的家庭里去照顾,这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是健康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当时想的是,让他去家庭里,能有更多与人接触的机会。
刚开始时这个家庭还是很高兴的,反正自己也有疾病,还有400元的补助,多少也能帮助到自己的家庭,所以也很乐意。但一段时间后,孩子又被送回来了——毕竟是有病的小孩,大人有病她可自控,但小孩子有病他不能自控。所以一段时间下来他们觉得还是不要占400块钱的便宜了……就把孩子又退回来了。退回来后,就由张颖女士一直在照顾他,一直到现在。
基督时报:当时孩子也是有在服药的是吗?
米子:那个年代,一开始是没有孩子吃的艾滋病的药物,孩子服用的是成年人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药。
基督时报:影片获奖后,对孩子们的生活会有帮助或改变吗?
米子:这个片子是2007年获奖的,从03年到07年之间有四年的时间,孩子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波折,也经历了很多的转变。高俊的奶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世了,他就彻底成为了孤儿。
2006年开始,彭丽媛女士去阜阳考察,关注这群艾滋病小孩,从那之后他们的命运就有了质的改变。现在高俊这个孩子十几岁了,已经正常上学。张颖知道他喜欢画画,又送他去学画画。现在他生活可以自理,虽然还要继续用药,但至少他是健康的。
我们当时仅仅做的,就是跟踪记录他的过程里,让这个孩子从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笑容,到最后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像家人一样,看到我们来就非常高兴,一直跟在我们的身后。
其实获奖之后也没有给到孩子特别多的帮助,但值得一提的是,06年开始,我们的行动被更多的爱心人士给延续下去了,更多的爱心人士都参与到关艾、防艾当中来。
基督时报:您当时拍摄整个记录片时,有碰到让你觉得很感动的事情吗?
米子:其实感动的东西也是痛苦的东西。最大的感动就是能有机会走近这群孩子,能看到他们从死亡边缘慢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看到身边本来是隔离、漠视这群孩子的人们,成为爱心人士走近他们,慷慨解囊从不同方面来帮助他们。
第一年我去时看到的几乎都是隔离的状态,包括那时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阻隔——那个村的村干部实际上并不希望我们去关注这些小孩,去拍摄这些事情,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家丑,不想让大家知道。因为那时公众只知道河南有艾滋病,并不知道阜阳也有,我也是去了才知道阜阳那几个郊外的村落都有艾滋病患者,都是卖血感染的。
那时我们拍摄,最开始是被追赶、被举报,后来时间多了,村里人也可以坐下来跟我们聊一些,也开始关心这些孩子,这个转变真的让我很感动。一开始虽然他们很漠然,好像这些事情跟他们无关,只要他们自己家里没有艾滋病就可以了,到渐渐的他们也开始对这些艾滋病孩子关注了,哪怕是打个招呼、停下来看一眼,也是很大的进步。
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一小部分事情,最初做这片子也不是为了送奥斯卡,而是何大一博士的一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工作,希望能作为一个艾滋病研究的学题——因为当时还没有艾滋病儿童的药。我们跟一些艾滋病研究机构有接触,片子做下来以后可以送给一些医疗机构社团、学校等,让更多人知道这群人,并去帮助他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理解和接纳艾滋病人。后来在一次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主办方放了这个片子,得到了几百名艾滋病专家和与会会众的认可。这让我们团队觉得应该让片子发出去被更多人关注。于是,美方导演杨紫烨就在美国做了放映,才得了奥斯卡。

(《颍州的孩子》纪录片封面)
基督时报:您当时拍完这个题材,是想向公众传达一个怎样的讯息或声音呢?
米子:第一,当时这一群人是被边缘化的。我跟踪他们的两年里,真觉得他们不能被边缘化,虽然他们有疾病,但他们是无辜的。我想应该要让更多人消除对艾滋病的错误认知,消除他们对艾滋病人歧视的态度——真的是歧视的,甚至是连走近这群人都不愿意的,是隔离的。艾滋病人其实不可怕,他们不是怪胎……我希望有更多人通过影片认识到他们,帮助他们。
第二,当时没有孩子的药,而何大一博士正在做这方面的医学研究。我们希望片子出来后有更多的医疗机构能用他们的专业帮助到孩子获得救治。这些孩子当时吃的是成人的药,而成人的药是有抵抗性的,剂量到底是多少?谁也不知道,就是自己觉得应该是这么多、应该是那么多。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成年人和小孩死去了,我们每次去,都有新的坟墓出来,每次去都有出殡的画面。
第三,当时帮助这些孩子们的张颖女士其实也非常困难,但她咬着牙坚持将孩子带过来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像张颖这样的爱心人士出现。
我特别高兴的不是拍了这个片子,也不是得了奥斯卡,而是看到了孩子们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健康地成长。现在楠楠有了自己的家庭,她通过母婴阻隔有了自己的宝宝,高俊也长大了,开始画画办画展了……
基督时报:请问您是基督徒吗?
米子:目前我还不是,我有个朋友是基督徒……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在我这里信仰是没有区分的,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人心应该是要向善的。
笔者后记:
其实很多人染上艾滋病,跟他们生活是否检点、道德是否败坏无关,但他们在染病之后却被迫承受来自人们的异样眼光,也被迫被人以“异类”相待。
以前,“艾滋病”是一个高危话题,也是大众不敢触碰的禁区。患者害怕被人歧视、看不起,就选择逃避,不去检测;不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人也害怕被“传染”,因而疏远、回避……在与米子老师交谈的前后时间段里,笔者在网上搜索了关于艾滋病各方面的知识,才对这个疾病有了初步的正确了解。也同时知道,现在虽然还没有治愈艾滋病的新疫苗和方法,但著名的“鸡尾酒疗法”已经可以暂时支撑住艾滋病携带者的生命,而日益成熟的母婴阻断技术也让更多的婴儿健康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新的成果和发现在层出不穷的诞生中,笔者也想在此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了解艾滋病,不要有歧视,让艾滋病携带者们能够勇于承担和检测,积极配合治疗。无论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有责任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弱势群体。对于艾滋病患者同样如此:多一些了解,少一些惧怕;多一些关怀,少一些歧视!给与艾滋病患者真切的支持、帮助和希望,让所有人都能生活在零歧视、零艾滋的世界里!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